一、口头合伙惹纠纷
甲与乙曾是同学。2021年7月,乙主动联系甲,提出共同投资开办一家托育中心。乙极力强调该项目前景广阔,并声称享有政府补贴,“稳赚不赔”。
基于多年同窗信任,甲很快被这个看似靠谱的投资机会打动。双方经过口头协商,约定共同出资150万元:其中乙出资120万元,占股80%;甲出资30万元,占股20%。双方还约定,所有资金统一存入指定账户进行管理,并于每年12月31日进行利润分红。
协议达成后,乙很快于2021年7月27日注册成立了一家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但令人意外的是,乙并未按照约定将甲登记为股东,而是将全部注册资本记于自己名下,由自己单独认缴。这意味着,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甲与这家公司并无法律上的股权关联。
尽管如此,基于对乙的信任,甲自2021年7月起,陆续应乙的要求,以“投资款”名义向乙支付了多笔款项。截至2022年8月,甲共计转账67万余元,远超最初约定的30万元出资额。甲曾多次询问公司经营情况及资金用途,乙从未提供明确的账目信息或分红方案。
随着时间推移,甲逐渐察觉情况异常。乙开始回避沟通,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最终彻底失联。甲公司陷入了投资款石沉大海、合伙人不知所踪的困境。
在多次尝试自行协商无果后,甲最终选择委托亳州分所的刘兴志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二、一审诉请被驳回
甲的律师整理相关证据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解除与乙的合伙关系,并要求乙返还全部投资款67万余元。甲方认为,乙未履行合伙协议约定,未进行股权登记、未提供账目、未分配利润,且彻底失联,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伙目的无法实现。
然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却驳回了甲的诉讼请求。法院的理由在于:原告甲与被告乙之间构成个人合伙关系,但合伙尚未进行清算。根据法律规定,合伙财产在清算前属于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只有在清算完成后,才能明确各方的权益余额。
因此,在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法院认为无法确定乙是否应当返还投资款及具体金额。
这一判决结果对甲而言无疑是打击。尽管乙始终未露面,也未提供任何公司经营及资金使用的证据,但由于甲无法自行完成合伙清算,其诉请便难以得到支持。
现实中,许多合伙纠纷中的当事人正是受困于类似的困境:负责经营的一方拒不配合,甚至下落不明,导致清算程序根本无法启动,而无辜出资人则可能面临“求告无门”的窘境。
一审判决虽然符合形式上的法律逻辑,却未充分考虑到乙作为实际控制经营和资金的一方,对合伙事务的进展情况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其拒不配合的行为实际上阻碍了清算的进行。如果一味要求原告承担清算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三、二审改判支持诉请
显然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偏差,刘兴志律师建议当事人继续上诉。当事人坚定地想要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在律师的建议下果断提起了上诉。
刘律师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在上诉意见中重点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
第一,涉案合伙属于“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合伙法律原理,此类合伙应视为“不定期合伙”。对于不定期合伙,各合伙人均享有随时解除合伙关系的权利,无需对方同意,只需提前合理通知即可。本案中,甲通过起诉方式请求解除合伙,已履行了解除程序,双方合伙关系自起诉状送达乙时即告解除。
第二,关于合伙清算的举证责任问题。乙作为合伙事务的实际执行人,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资金使用和财务账册的保管。在甲多次要求查账和分红的情况下,乙拒不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甚至失联,明显存在恶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乙对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亏状况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乙无法提供合法、真实的账目资料,导致合伙财产无法清算,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法院可以推定甲的主张成立,判决乙返还甲所投入的全部资金。
二审法院采纳了上述代理意见,乙未提交原始账本等任何证据证明合伙经营状况、资金使用情况或亏损事实,其行为已导致合伙清算无法进行,此不利后果应由乙承担。同时,鉴于双方合伙关系已解除,乙应向甲返还其投入的款项。
最终,二审法院作出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甲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乙向甲返还投资款67万余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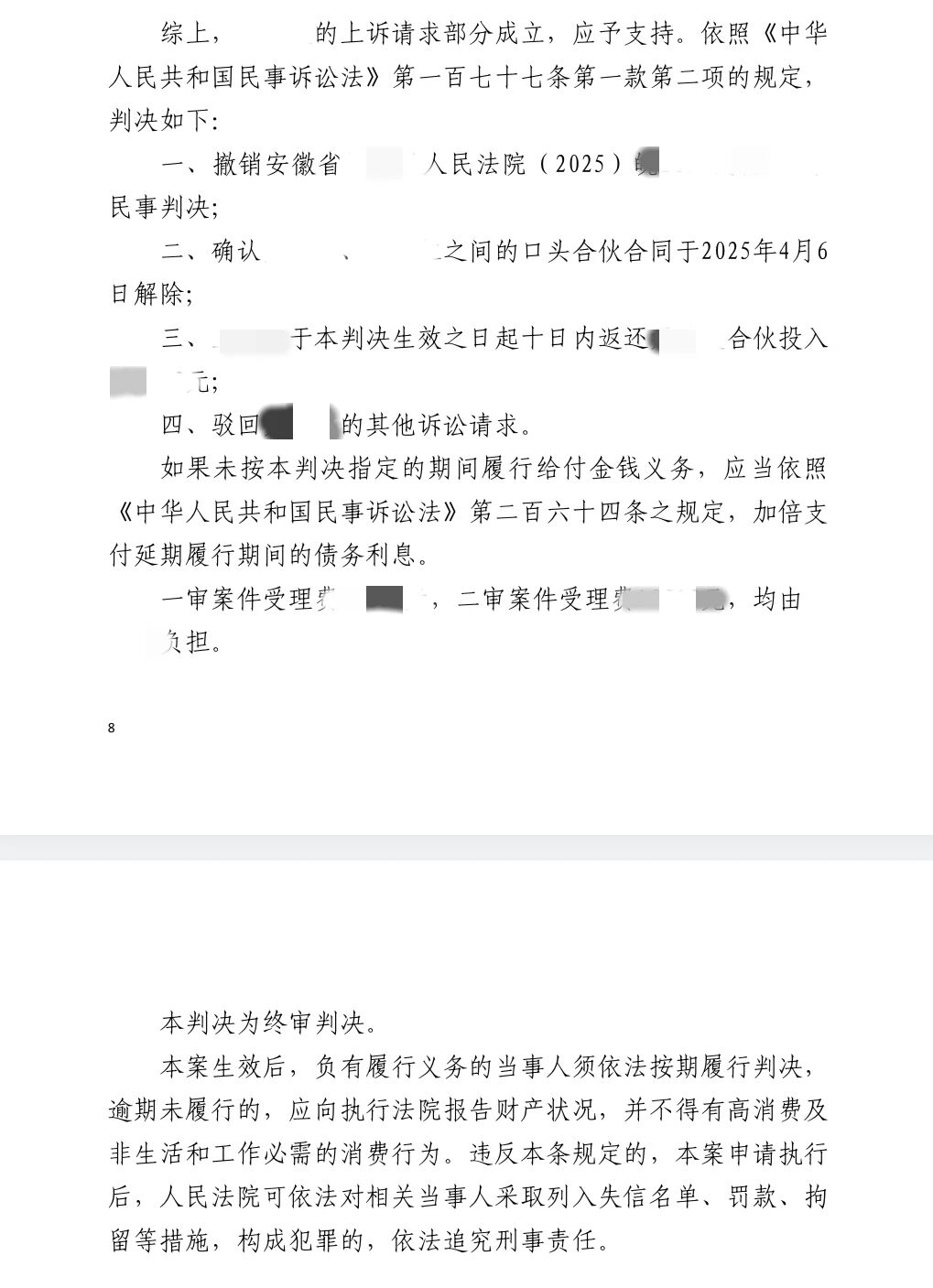
这起案件不仅为当事人挽回了经济损失,更具有重要的法律启示意义。口头合伙隐藏巨大风险,投资者应尽量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出资额、股权比例、职责分工、分红机制和退出方式,并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以固化权益。
同时,作为负责经营的一方,负有诚信义务和相关举证责任,企图通过“玩消失”来逃避责任,最终很可能在法律面前无处遁形。
而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本案二审判决展现了法院在个案中如何通过灵活运用证据规则和法律原则,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避免机械司法,最终实现实质公平。在不定期合伙的解除、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认定上,该案也为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裁判思路。法律不仅是条文,更是保护诚信、惩罚失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